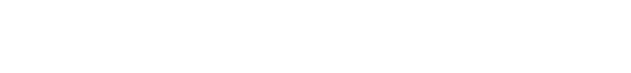今年是我在上外的第二十六个年头了,也算是见证了母校的种种变迁。松江校区从无到有,就连虹口校区也已全然变了模样。记忆中的牛津中心被夷为平地,那栋藏在校园一隅的研究生教学楼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也许,没人会再去怀念那两个破旧的地方了吧。而它们于我,却是我在上外最珍贵的回忆。
我本科入学那一年,太阳成tyc7111cc的院长是何兆熊老师。初识何老师应该是在新生见面会上,那个最大的阶梯教室,我们热切而清澈的目光追随着老师缓缓走上讲台。那种自内向外散发出的谦逊、儒雅和博学,让我一下子就对这位和自己同姓的院长充满了好感。
大三时,何老师给我们上语言学课。大家一面感叹他深厚的英语功底,一面欣赏他不温不火的风格。应该说,做何老师的学生是幸运的,但也是不轻松的,很少有学生能得到老师的当面夸奖。所以一次课下,我因问了一个语用学问题听到何老师的一句“好极了”的时候,内心的喜悦与鼓舞实在是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。
后来,我顺理成章地读了语言学的研究生,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老师的弟子。老师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严格,批改论文比我们自己都要认真不知多少倍。我的一个师兄最怕何老师了,据说他每次跟老师见面或通话都会脑门冒汗手心发凉。我刚好相反,感觉跟老师相处更像是家人。博士毕业那年,老师把语言学课交给了我。那时常有学生以为,我是老师的女儿。是因为同姓“何”吗?还是老师和我的祖籍都是“广东南海”呢?
也许真的有所谓的命中注定吧,让我得以在老师身边,耳濡目染他的淡泊与从容。他一次次让我在喧闹浮躁的环境中安下心来,去追求一种清醒、清静的人生境界。

图/我们和我们亲爱的导师
沿着昏暗老旧的楼梯上到三楼,左手最里面那间教室就是李观仪老师的“教学法”课堂了。教室不大,学生也不多。除了几个旁听的本校老师以外,正式选课的学生只有四个。那时候选课也没多想,只是觉得以后要当老师的话,教学法总需略知一二的,何况是李先生亲自授课。后来才终于慢慢体会到,这门课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全方位的修炼。其一,上课绝对不允许迟到。别说迟几分钟,只要上课铃声一停,迟几秒钟也是不能进入教室的。其二,学期作业量极大。毫不夸张地讲,整个学期仅这一门课的作业就足以让人疲于应付了,而那个学期我选了九门课。其三,课程成绩偏低。我记得第一次考试大家都只有六七十分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全班最后一名,相互偷偷打听之后才暗自有些安慰。
正是因为一直感觉自己在这门课上的努力始终不得要领,所以学期末的论文确是下了些功夫的。我去学院一些老师的精读课堂上听课,把所见和所想认认真真地记录下来,最终形成论文。那时的实证研究不容易啊,没有录音录像什么的。碰到比较热心容易沟通的老师还好,有的老师是根本不接受我这样贸然的请求的,这个时候就只能厚着脸皮软磨硬泡好话说尽了。幸好,这些折磨没有白费。论文的成绩是真的想不起来了,只记得当时李老师说把我写的东西转给了一些相关老师看,或对课堂教学有所帮助。天哪,那一刻,所有的辛苦都值了。
而后的两三年间,和老师没怎么见过。毕竟,我那时还没有留在学院。只是有一次碰巧路过李老师的办公室,她笑眯眯地跟我说还记得我,她的书橱里还留存着我的那篇期末作业。
生活区的五号楼是最早的一栋研究生宿舍楼。那时读研的人少,硕士博士加起来也住不满。一二层住男生,上面四层住女生,偶尔还有一家三口入住的。楼上楼下其乐融融,彼此也有很多熟识的机会。我当时有可能“混入”王德春老师主持的语言学讨论会怕也是因了这个缘故。学院所有语言学方向的老师和博士研究生每周固定时间聚在一起,每次一位主讲,之后是大家的提问和讨论。主讲人的准备充分,提问者的问题尖锐,常讨论得面红耳赤,压轴的是王老师精辟的点评。我那时还在读研二,又是个“外来户”,大多只有聆听的份儿,话是绝计不敢乱说的。尽管如此,王老师还是很快记住了我的名字,他喊我“小何”。
老师关心参加沙龙的每一个学生。除了学业上的指导,还经常充当“收发室的大爷”,把积压在学院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取的信笺顺带拿给大家。我的毕业论文快完成那会儿,便受到了王老师的“邀请”,他鼓励我做一次讨论会的主讲。已经记不清当时有多么紧张了,只记得那天拉上了我的好朋友朱磊去帮我壮胆。几位老师的提问言辞犀利,一针见血。我当然知道他们一向如此直接,但那个时候面皮儿薄,只觉得被他们问得鼻子酸酸的,眼泪顽强地在眼眶里打转。王老师的点评在最后。老师宽厚的嗓音和亲切的笑容让我反而忍不住落泪了。有那么一瞬间,感受到的像极了父亲般的慈爱。
我们那一届读语言学的硕士生一共十个,五男五女。大家关系很好,经常有各种理由聚在一起。最常见面的地方应该是牛津中心了,那时学校存放所有英文原版书刊的小图书馆。一幢不怎么起眼的小平房,一簇簇并不太明亮的灯光。我还记得他喜欢坐的那个远远的位子,我还记得他在我的书签上留下的字迹,我还记得他们,她们——我们其实早已习惯苦读时彼此默默的陪伴。

图/我们班的语言学小分队
那时的我们确是勤勉上进的。束定芳老师的语义学课下,我们总有没完没了的问题围着老师问。束老师真的耐心啊,经常被我们缠着几十分钟才能“脱身”。毕业论文完成后,大家自发组织了十场“预答辩”,为每个人的论文把关。我们公开的那场模拟答辩,梅德明老师也来“旁听”的。我真正论文答辩时的主席是许余龙老师,一位让我又敬又爱又怕的老师。许老师平时话不多,为师也算不上凶,可随便哪篇语言学论文交由他审阅,他很快就会发现问题,而且通常是论文中最关键、作者最怕被问及的问题。于是,一个来小时的硕士论文答辩,导师正襟危坐,答委题题惊心,听众屏息凝神,那场景应该算得上很有仪式感了。
答辩,毕业,各奔西东。人去楼空,沉淀下来的唯有师生情和同窗情。感谢有你,我从未遗忘旧时的清白脸庞;感谢有您,岁月不曾湮灭年少的清澈目光。我想回头望,把故事从头讲。时间迟暮不返,人生已不再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