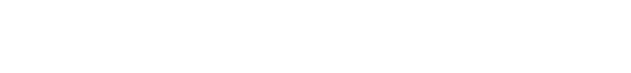章振邦教授简介
章振邦,男,1918年生,安徽合肥人,教授、曾任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主任。
1940年至1944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学习,毕业获学士学位。1944年至1946年间在武汉大学外文系任助教,1946年至1956年间,先后在安徽大学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江淮分校、安徽师范大学任教,1956年进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,1985年被评为教授,1987年离休。
主编《新编英语语法》系列丛书,包括《新编英语语法》、《新编英语语法教程》、《新编英语语法概要》,《新编中学英语语法》,等等。在《外语教学与研究》、《中英语文教育》、《外国语》发表英语语法研究方面的论文十余篇。
采访人:章老师,您好。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。首先请您谈谈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习英语的?
章振邦教授:那我学英语可早了。在小学的时候就学英语了。是家里请的老师教的。因为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在铁路上工作的。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,铁路是洋务,打个报告都要用英文。但是,我的父亲不懂英文,就要请人代笔。那就要花钱。哪怕写一个请假条都要花两块大洋,如果再长一点就要五块大洋。从小我的父亲就觉得“我的孩子一定要把英文学好,不然今后寸步难行”。所以从小就请人教我们英语,那时候还在北京。所以,我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。当然,小学学的英语只有那么一点程度,后来中学、大学继续学。
采访人:当时在小学开始学英语时,您觉得整个社会学习英语的环境怎样?
章振邦教授:我们在小学的时候,学校和社会对英语都是很重视的。只是当时不论是教学方法还是教材都比较落后。
采访人:那么后来您考进了什么大学呢?
章振邦教授:武汉大学,那时候叫国立武汉大学。当时武汉大学外文系很强。当时是抗战时期。武汉大学搬到四川乐山。尽管如此,当时武汉大学教师阵容非常强,图书资料非常丰富。因为它原来在武昌,抗战的时候把所有的图书都搬到乐山,所以当时阵容很强大。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上面就提到当时在乐山的武汉大学,尤其是它的外文系,很强的。比如我的导师就是朱光潜,非常严格的。我们读他的《英诗》,叫背就得背,不背在课堂上愣着就很尴尬。还有一个,比如他教我们翻译,比如Charles Lamb一篇什么文章,他的东西都是比较深的。一篇文章,大家都要翻,他自己也翻,然后上课的时候,反正班上人也不多,就那么十几个人,这一句你怎么翻的,第一段你怎么翻的,你要念出来,然后你又怎么翻的,大家念。然后,他自己也念他是怎么翻的。这样教的,很严格。所以当时我们在武汉大学学的几年,还是受了一些很严格的训练。
采访人:当时在武汉大学学习的过程中哪些课程您觉得印象很深刻?
章振邦教授:当时学的东西和我自己个人努力的方向不一致。我从小就喜欢搞语言。但是我们进的外文系完全是文学课程,完全是英国文学。比如说,光是英诗,我们就学了朱光潜教的普通英诗选读,后来又有方重教的英语长诗。再比如说戏剧,我们就学了近代戏剧、希腊悲剧、希腊神话、莎士比亚。当时学的东西很专门的,都是文学方面的东西。但是我自己努力的方向呢,还是在语言方面,我总觉得要把语言这个东西搞透。所以后来,我在工作当中,就是教书,文学没有用上。当然,读过文学对我语言的发展很有帮助。但是,这个帮助是在比较深奥一点的文学语言方面的帮助很大,而在口语方面帮助不大。我觉得几年当中读下来,我觉得散文,尤其是小品文,像Charles Lamb,Goldsmith的,这些人的作品我读得很多。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当代英语,还是作为文学作品读的。
采访人:您能不能回忆一下,在您大学期间,以及后来您刚刚参加工作期间,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、您特别敬仰的老师?
章振邦教授:我毕业的时候留在武汉大学作助教,教一年级的基本英文。当时,我的老师当中,朱光潜还在那里教书。他上课我还去听,他给三年级、四年级教翻译我都还去听。还有几位老师,我和他们平时往来都是比较多的。有一位历史系的老师叫杨人鞭,历史系教授,他过去教过我们世界历史。毕业以后曾经有一度,感觉到由于历史基础不够,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深度不够。所以我曾经下功夫学欧洲史,就是他指导的。所以我受他影响很大。我每两个礼拜要到朱光潜家里去一趟,每次都要问你,这两个礼拜读了什么书,要注意什么。这两位对我影响很大。尤其,杨人鞭是历史系教授,但是后来我在学校教书,所以就拜他为师了,他指导我怎么样学欧洲史。当时最新的一套欧洲史,编著人叫Fisher,三大本,我很认真的读了。从头读至尾,很认真地读了。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请教他。这个对于我,对于那些文学作品的理解帮助很大。这个对于我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,比如说法兰西阶级斗争,雾月政变,这样的一些书,帮助都很大。因为我知道当时的历史知识、历史背景。否则的话,那种书很难读的。
采访人:那么,后来您在教学和研究都是选择了英语语法这个方向。这么多年坚持下来,您觉得动力何在?
章振邦教授:对我来说是这样,搞语法的研究是与英语教学分不开的。你要教英语,你要把东西教透,有一些语法现象,你不能不知道,如果这些方面不知道,你怎么教书呢?有好多东西你就没有讲深讲透。而且更重要的是,后来,我们要编英语教材,英语课本。编英语课本,你不得不涉及到语法,因此逐渐在这些方面就比较重视。当时,我在英语系工作,主要做的是两件事:第一件事,就是在“文革”以前,我主要是搞教学方法的改革,这个改革当时叫做“听说领先”,就是怎么样使我们学生能够听得懂、讲得出,加强听说方面的基本功训练;“文革”以后一直编教材,所以比较着重于语法研究。因为这个语法研究啊,实际上,比如搞翻译,好多地方要用到语法,有好多地方翻译得不对,它这个语法结构没有搞懂,所以就翻错了。所以慢慢地就在这些地方下一些功夫,因为你要编书,这些东西不得不学。
采访人:那么这个是不是和您本来就对语言规律感兴趣有关系呢?
章振邦教授:是的,我对语言规律更感兴趣。就这个方面,武汉大学外文系,她的教学的倾向性就不如复旦大学。复旦大学教语言,有那么几把手教得比较好,比如张月祥老师。我们武汉大学,都是搞文学,当时的小说是陈源教的,戏剧是袁昌英教的。这些人都是搞文学的。他们偏向于文学。但是我还是努力于怎么样把语言搞好。所以跟这个和文学的路子有一点不一致。但是,到后来也不得不读,到后来学文学也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。但是毕业以后都是教书,毕业以后都是教语言。
采访人:和以前相比,您认为英语学科发展的怎么样?您有什么评价?
章振邦教授:现在这个英语学科的发展当然跟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。现在最好的一个做法,大概许多学校都是这样,就是重视语言教学。不像过去,那个外文系,它都是搞文学比较多,现在重视语言教学。而且,现在重视听说训练,学生交流能力增强,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加强了。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呢,就是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,我们的知识面比较窄,就是对于语言知识本身也很不够的。比如说像你们现在也教语法,你们教的《新编英语语法教程》,后面都是和翻译、写作、修辞都是息息相关的,但是现在这些方面好像不够。再加上现在又有人提出要淡化语法。这个东西被别人一理解,就理解成现在教英语不要语法了。不教语法了,就是对语法轻视,这个长久下去会引起很多的不良后果。人家英国人讲,当初communicative approach的创始人,他们搞这个交际法,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,在广州外国语学院,现在的广州外贸外语大学,他们最开始搞交际法,叫做communicative approach,他们就不要语法了,就完全教authentic language,就是教真实的语言。结果1981年我们到广州开会,试点班的学生讲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。后来英国的专家来,我们会见他,他说,我们搞交际法并不是不要语法,并不是不要语言教学,语言的规律还是要教的。所以后来广州外语学院后来也改弦易章,还是要重视语言教学。所以在我们这儿,李观仪老师编的《新编英语教程》,在这里头就有一个主导的思想,这个主导思想就是,教学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应变能力,口语能力,交际能力,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呢,这个语言方面的训练,包括语法方面的训练,还是要按部就班地教的,而且还是要认真教,要把它教好。所以这就是李观仪主编的《新编英语教程》的主导思想。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有些人在观念上认为语法这种东西不重要,只要你会讲就行。你要细细地研究起来,如果长期下去,我们的学生英语的基础会受到很大的影响。如果他一些基础的语法概念搞不清楚的话,我们学的好多东西,都会有问题。我们的老师,如朱光潜,过去在教我们英诗、翻译之后有许多问题,有许多问题都是语法问题啊。你比如说,这个modification,修饰,transferred modification,像这一类东西,你要不懂,没有这个方面的知识,你就看不懂,看不懂,翻译就翻错。所以现在有些人,好多东西他不懂。我们现在讲语法这些问题啊,已经不是时态啊,这样的一些问题,再高出一步,是修辞问题。你不懂就有好些东西不理解。我举个例子,你比如说,the city of Rome,这个of代表什么?这个of它是作为一个并列结构的一个桥梁,你如果要不懂的话,有好多东西翻不出,翻不准,甚至于能搞错。所以呢,现在我们的学生恐怕在这个方面知识不够。但是呢,讲语法修辞这些东西,你又不可以过分地去强调,关键还是口语要流利,翻译要准确。但是你要做到这些方面,语法修辞这方面的知识不可以不知道。尤其是当老师,更是要知道这些方面,不然你怎么教学生?
采访人:您了解目前上外的本科课程设置吗?您觉得目前的上外本科生的课程设置有什么发展,存在什么问题吗?
章振邦教授:我觉得呢,当然,我现在也不是很了解,长期以来没有在第一线教学。感觉到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,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,在大学阶段,尤其像上外这样的重点大学,我们所教的英语到底是什么英语的问题,是专业英语还是普通英语?比如能考上我们学校的同学,他在中学都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英语基础,否则他考不进来,如果进来以后,我们教的大学英语啊,还有四级六级英语啊,教的和考试的都还是普通英语,这就成问题了。所以一年级的同学就感觉到没有事可做,好像我们现在在学英语,人家一般的人都在学英语,我们学英语到底有什么区别啊?感觉要学的东西没有学到,感觉得不到啥东西,这个就是普通英语。我始终觉得像我们学校这样的一个学校,尤其是英语专业,不仅是英语专业,其它专业也是一样,一进来应该要教专业英语。当然这个专业英语是跟专业密切相关的。比如,经贸系一进来就要学经贸方面的,这里头也有一套基础的词汇,基础的语法结构,基础的东西,然后有比较高深的东西,你学了这一方面的东西以后,毕业生出去就能够应付商业谈判、外贸谈判。比如,学法律系,或者学国际商法,你一进来就要学这一方面的英语。你这样的英语学下来,今后到工作岗位上,一到岗位上,就能用得上,否则的话就用不上。比如,要和外国人对簿公堂,你学的普通英语根本不够,你的语言根本不是人家经常用的那套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学校,学生进来应该要学专业英语。你就拿我们英语系来讲,语言啊,文学啊,你也可以学专业的东西。专业英语有好多东西要学得比较高深一点的,比如语言理论,都要学比较高深一点的东西。而我们现在呢,一进来还是教的普通英语。四级考试是普通英语,六级考试还是普通英语,甚至八级还是普通英语。你没有跟你的专业联系起来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前外语教育战略上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当然这个问题对我们这种学校不成问题,对于其它的学校可能是一个问题。比如内地的一个学校,进来的学生未必过关,他还要学一点普通英语,这个就涉及到中学阶段的英语,你怎么学,学到什么程度,这个学校招生,招进来英语的门槛要多高?如果门槛比较高,那么一进来之后就是专业英语,如果英语门槛不是很高,那当然还要学普通英语。但是,普通英语也不能四级、六级甚至八级,都是普通英语,那不行的。英语一定要和他的专业挂起钩来。所以我认为普通英语和专业英语的问题现在是一个大问题。你就拿文学系或者翻译系,你翻译系一进来你就要研究汉英对比,语法结构的对比,修辞的要求的对比。这种东西教了,有助于他提高翻译水平。所以光搞普通英语,学生感觉到不解渴,不能解决我的问题。所以呢,特别是一年级的同学感觉到好像在一年级非常的轻松,无事可做。有一回,还是李尚宏老师带我们到松江去,和学生座谈,学生就提这个问题,我们现在学的英语和外面人家学的英语有啥区别?就是这个问题。应该是专业英语,就是文学专业走上来应该学文学语言,在一般的语言基础上搞文学语言。你要是搞翻译,那你语法修辞方面的东西都要好好搞,不然的话,你翻译怎么跟上?现在的问题,这个涉及到一个战略问题。因为涉及到高中英语应该达到什么水平。但是呢,中国这么大,各地的水平不一样,你要一刀切,到高等学校就教专业英语,这也不现实。因为什么呢?因为专业英语必须建立在普通英语的基础上,如果他普通英语的基础都不牢固,你一下搞专业英语,他跟不上。但是像我们这种学校,完全可以啊,这个时候还在搞普通英语,这是浪费。所以我们的问题,我常常讲,我们的英语教学最大的一个问题,就是时间长,效率低。你想想我们从中学学了六年,小学不算,大学四年,这十年都是普通英语啊,英语和专业没有很好地连接起来。所以呢,这个是当前很大的一个问题,当然这个问题要解决呢,恐怕不是我们一个学校所能解决的,因为大家都要四级考试、六级考试,它考的都是普通英语,而且普通英语呢,还是教育部统一出题,你怎么办?所以要上级领导部门对这个问题…否则的话,我们怎么提高?我们的第二外语又该怎么学?我们英语专业起码还要一个外语吧,法语、日语或其它的语言,你都还要学吧?你还在搞普通英语,那么第二外语呢?学的深度不够。第二外语有时候就不能够解决问题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普通英语与专业英语的关系问题。尤其对于我们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学校来讲,老路子如果还走下去,我们的水平老是提不高。我们的学生,比如经贸系的学生,一毕业出去,你马上就能够参加一个外贸谈判;我们的法律系的同学,毕业出去要能够和外国人对簿公堂。不能够还要人家继续培训才能够达到这个要求。所以我们现在提国际化的创新型外语人才,你这个英语教的还是普通英语,这都是一句空话。你怎么达到?
采访人:您对我们青年教师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吗?
章振邦教授:我对我们现在的青年教师情况不大了解,据说流动性很大,哪里待遇好一点,就不一定在这里干。这样呢,我们就留不住人,我们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就不能得到稳步的提高。过去不大一样,你留在英语系教书,这一辈子就在英语系了。我要好好学习,我要站住讲台,把我的书教好。现在人的想法不一样了,毕业要想买房子,就拿这几个钱那怎么行啊?哪个地方待遇好,我就跳槽跳走了,所以师资队伍如果没有稳定性,队伍就培养不起来,过去我们一个教研室里,都是老中青一代带一代,这样呢,我们的教师队伍是整齐的,而且后继有人,老一代过去了,年青的一代上来了。包括像戴伟栋这些人都是从一年级教起的。我们培养人,哪个人学什么,科研搞什么,都是有一定的方向。比如我过去在英语系工作的时候,我就安排了侯维瑞教授,那个时候他也是我们一般的青年教师,我问:“你的兴趣在哪里?”他说:“我想搞文学研究。”他呢,就专门研究文学。结果他后来很有成绩。还有一个人,他是搞修辞的,我们科学研究专门有一个修辞小组,杨小石,他们几个都是修辞小组。结果这位教师,他是59届的,他在修辞方面出了好几本书,研究生、博士生导师,现在很有成绩的。叫什么名字?凡是教研室里,老中青队伍整齐的,而且教学和科研都是分配得比较具体的,都是落实到人的,都能够搞出来名堂,都出了很多书。相反地,如果一个教研室里,尽管每个人讲起来,水平都不错,但是没有形成一个队伍,谁也不听谁的,各人搞各人的,结果呢,在这个教研室里就搞不出名堂。像翻译教研室,我们英语系的翻译教研室水平很高的,好多人的翻译水平都是很高的。但是你不听我的,我不听你的,各搞各的,结果翻译组编不出来东西,连一本翻译教材都搞不出来。就是没有形成一个队伍。所以我认为现在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还是要老中青相结合,还是要教学任务、科研任务都要落实到人。还有的事讲了都很伤心的。我刚才讲的侯维瑞教授,他后来得了肝癌,我当时也生病,住在瑞金医院,他住在五楼,我住在六楼,我下去看他,他说,你当初安排的那个科研任务,我现在搞出来了,编了一部英国文学史,这个书始终没看到,他说“我完成了”。当时讲这个话都流泪。所以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一定要方向明确而且要持之一恒,使他很稳定,这样才能培养出来人。否则的话,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。哦,胡曙中。当时杨小石带他,结果杨小石出国,在国外待了十年,什么也没编,结果胡曙中倒把修辞给编出来了。这个就是说青年教师要有一个方向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教研室的组织有没有这样严密?如果不严密,人就像走马灯一样,今天调到这,明天调到那,他不稳定,他的学术上的发展就受到影响。过去上课,比如哪个教研室哪个新来的老师上课,我们都要去听课。听过之后,要和他讲,你今天哪里讲得好,哪里讲得不够。希望你以后再提高。这是帮他,使他教书一堂一堂课都能有所改进。现在你是你,我是我,大家各教各的。这样就不行了。所以要老中青结合。还有呢,现在从外面聘请老师,一年给他五十万,怎么样怎么样…我上回就和吴友富他们讲,其实啊,从国外聘请一些专家,充实师资队伍,这种做法是可以的。但是主要的还是靠我们现有的师资队伍,提高他们,培养他们。你不能把眼睛放在国外,那种人教书不一定教得好。这样一些人聘请来充实我们的队伍是必要的,但是主要的还是我们现有的师资队伍中,怎么样提高他们、稳住他们,使他们在教学中不断地成长。还有一个呢,就是现在好像,我在那篇文章中也讲过,好像说我们学校今后的办学方向是“科研教学型”,而北外呢,是“教学科研型”。我讲,科研教学型也好,教学科研型也好,你都要保证质量啊。你现在搞一些人,关着门在那里搞科研,这些人不关心教学,不上课,专门在那里搞科研,这种科研搞出来是脱离实际的。再说,我们学校如果搞科研教学型,那就是科研是第一位的,那我们的科研和中科院的科研有啥区别?我们是教学单位,首先应该以教学为主,科研要为教学服务啊。所以,这种提法都有问题。科研教学型也好,教学科研型也好,教学与科研不能分开,据说,现在就有一帮人,在那里头专门搞科研,脱离实际。科研一定要为教学服务,科研的成果一定要运用到教学当中去。这个教学是指本科生教学、研究生教学,一定要能提高,不然怎么提高质量啊?如果教学和科研把它对立起来,这个我觉得就有问题。一天,有人和我讲,人家是教学科研型,我们是科研教学型。我就讲,你不管是哪一个型,你要保证质量,保证你的教学质量,包括你的本科教学质量,研究生教学质量。你只有科研为教学服务,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。这个里头是个问题啊。我觉得有许多问题啊,很值得注意。
采访人:谢谢您结合您的经历给我们谈了您的学习和教书育人,还有对上外英语学科的一些想法,非常感谢您。
采访人:葛忆翔 马乐东
整理:葛忆翔